老挝苗族华人社会身份的持续生成
老挝苗族华人社会身份的持续生成
来源:中国侨联
距今200年前后,西部苗族部分成员(即Hmong)自中国贵州、云南等地分批迁至素有“东南亚屋脊”之称的老挝高地生活,广泛分布在与中国、越南、泰国交界的上寮区域。其中,川圹(KhoengXiangkhouang)人数最多,华潘(Houaphan)、沙耶武里(Sayaboury)、乌都姆塞(Oudomxay)等次之。依传统服饰、语言特征等表征符号,他们分为白苗、黑苗、花苗、青苗、红苗等支系。
此后,为更好地促进自身发展,协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经过和多方势力的长期博弈,苗族最终被纳入老挝三大族系之一的老松族(Lao Sung),得到当局承认,从而实现了从“客居山民”向“法定国民”的转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替代种植”项目的扶持和政府的协助下,他们逐渐摆脱刀耕火种的传统游耕生计,强化了与市场之间的联系,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近20年,借助革新开放政策深入推进的机会,越来越多的苗族投身老挝国家发展浪潮,移居城市生活,整体发展步入快车道。截至2020年,其人口已超过60万,成为当地除佬族、克木族之外的第三大民族。
在从“边缘人”向“建设者”转变的过程中,老挝苗族虽克服了诸如文化差异过大、民族矛盾激化、国家意识模糊、自身发展缓慢等多重困难,但至今仍面临一大难题:在早已获得法律身份的情况下,他们却始终无法完全获取社会身份,从而导致社会身份呈现出显著的“持续生成”特征。
一、问题的提出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角色/身份”代表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关系,角色不同,行为体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的功能也不同,宏观观念结构通过个体身份角色映射出的镜像也有所差异,而随着个体角色身份的发展,集体身份终将形成。
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作为海外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地化过程中社会身份的形成既具有他群所展现出的普遍性,亦具有我群所独有的特殊性。“落地生根”作为获取居住国身份的最终表达是海外华人社会最重要的集体转型,对精英身份的追求,极大地促进了华人抛弃移居者思维,转而采取向移居国靠拢的方式为获取法定身份努力。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作为从少数(祖籍国)向少数(居住国)的转变,居住国为其赋予成员资格时亦会采取相对特殊的统合策略,如泰国就将生活在北部山地的少数民族集体冠之以“山地民族”之名,并推出相应的管理制度。越南、老挝则通过民族识别等方式将之纳入“少数民族”体系,在确认其国民身份的同时,进一步保障他们的社会权利。于是,被归置进民族国家版图,并接受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挑战遂一起发生。
在这样的情境下,少数民族海外华人正争取有尊严地被整合进国家发展中,既不脱离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又能获取国家身份和群体身份。但问题是,主流社会将他们视为野蛮落后的代表者的刻板印象,很难随着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建设而轻易消失,故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社会身份的最终获取,必然是在与所在国国家主体的协商与妥协、同主流社会诸多方面互动理解的基础之上寻求合适的发展机遇和空间。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具体实践中需要同时面对“国家”和“社会”两个主体。
然而,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尤其是对老挝苗族的关注明显不足。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三个主要方向:其一,探究他们在“秘密战争”中的表现,力图呈现每一阶段苗族的不同动向;其二,考究他们作为战争难民移居美国后所遭遇的集体困境;其三,考察留居老挝境内的苗族的族群文化。鲜少有人关注面对巨大的政治、社会压力,其面临的融入难题,少数涉及这一话题的著述依然将重点放在他们的社会组织、内部文化如何与老挝民族国家相自洽上,或止步于简单的城市化适应分析,几乎很难见到针对其身份问题的论说。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整合历时与共时视角,在对苗族于老挝所经历的“国家化”和“社会化”过程进行分析的同时,探究其社会身份“持续生成”的实践路径,以期为观察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在地化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视野。
展开全文
二、社会身份生成的前期准备:苗族在老挝的“国家化”
17世纪左右,苗族支系向中国南方边地的持续流动为他们提供了进入老挝的可能。待到达上寮等地生活后,随着与不同政治主体互动的加深,他们在法律层面的身份逐步得到认可,但强烈的异质性表现仍迫使其不断向国家靠拢。
(一)“国家化”前奏:苗族向老挝的迁徙
苗族向更南部的迁徙拉开了他们走向中国境外的序幕,而在进入老挝的过程中,苗族不仅受到自身生计方式的影响,也经受了战乱的洗礼,最终才到达新的定居地。
1.迁徙原因
不少学者认为,苗族向东南亚的迁徙是因战争的发生而被迫进行的,认为17-18世纪清王朝在西南地区非汉族群当中推行的强力措施,导致了湘黔交界“生苗”区的苗族支系向今广西西北部与云南东南部的迁徙,从而压缩了早已生活在此的“蒙人”支系的生存空间,使其最终选择越过边界进入越南与老挝北部定居。但实际上,从现今老挝苗族的历史记忆、生活遗迹并结合西方关于他们的早期研究资料来看,“战争论”的观点可能并不尽然。
历史上,苗族曾长期保持刀耕火种的生计模式,耕地严重依赖烧荒后的草木灰蓄积肥力,但通常3-5年内地力便会消耗殆尽,必须另觅他处以谋生;加之一般苗族家庭人口至少五人以上,若要满足口粮需求,开垦的土地面积必须足够大。周而复始,迁徙就成为苗族的常态。这也使得越境进入老挝等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谋生成为可能。从当前老挝苗族保留的传统生计方式推测,这种由耕作引起的流动曾在其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相对来说规模较小,多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
由此,战争的爆发可能一方面加快了他们的移动速度,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规模性迁徙。法国殖民者曾提到,“大约从1864年开始,老挝镇宁(今川圹)地区进入了许多不同旗号的中国军队,他们都是失败后从中国逃到老挝的,与他们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山民,包括苗族、瑶族等,他们此后在川圹高原生活了下来。”今天,赛松本的白苗亦传说他们很早之前生活在中国的远山之中,由于垦荒种地的缘故,种植几年,地力衰减后就需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于是就这样一直向南寻找土地,后战争发生,被带到了老挝。明显地,这种社会记忆从集体表征的层面呈现了具体生活与记忆符号间的历时性。
史实中这一历时性又是如何表现的呢?越南学者琳心提到,“1796年至1820年间,……苗族分两路迁入越南,一路包括黄、骊、王等姓氏的大约100户人家先到了河江省的同文县,然后一部分人又分散到河江省的黄树皮;另外一路包括黄、陆、周、崇、武、江等姓氏的80户人家迁到了老街省。后来,这一翼中的武、崇、江等姓氏中的30户人家又迁徙到了越南西北地区。这些苗族大都来自贵州,一部分则来自云南和广西。”其中不乏借道进入老挝上寮地区的苗族。法国人类学家李穆安(Jacques Lemoine)调查后认为,苗族“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发生在1868年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有一万多苗民从贵州经云南和广西进入了越南。这些人在越南的河江、老街、莱州、山萝、义路等省定居下来。一些人又向南迁到了安南北部的和宁、清化和义安等地区”此后,部分人可能越界进入了老挝北部生活。
由此可见,“苗族向老挝的迁徙是多批次的,而不是相对集约的;是零星的,而不是大规模的;是单线路的,而不是全方位的……不是由贵州、四川和云南其他地方持续不停地直接迁入老挝的。”这也从侧面说明,“生计选择”极有可能是影响苗族迁徙的重要原因,少则一两年,多则数年的农耕需要促使他们不停地迁徙,在这一过程中“一般都是先在云南文山(麻栗坡)和西双版纳(勐腊)居住若干年甚至上百年以后,再从这些地方迁入老挝北部”。而东南半岛北部广阔的山地则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土地保障,也极大地促成了他们的迁徙。
2.迁徙路径
以寻求适耕土地为目的的迁徙和战争移民的身份本让苗族很难有一致的迁徙路径,但从长时段的历史记录和遗留下的生活痕迹看,他们进入老挝的途径主要有东西两条。
生活在现华潘、川圹等老挝东北部的苗族,大部分是从云南东南部进入越南相邻地区,最后又再迁到老挝的;居住在丰沙里(Phong Sali)、沙耶武里等与中国联系紧密的省份的苗族,大部分是先在云南南部逗留经年后,再进入老挝的。
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呢?主要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一方面,从越南进入老挝的苗族刚开始时即生活在今天越、老交界的临近省份,在当地经营一段时间后,由于受法国殖民活动和生计需求的影响遂进行了二次迁徙。曾在印度支那地区传教并著有法语世界第一部苗族史的萨维纳(Le PèreFrançois Marie Savina)提出,“东京(现越南河内)所有的蒙人居民都是从云南迁来的,生活在老挝的苗族则是从东京迁去的。”另一方面,从云南进入的苗族很可能是沿着云南与中南半岛的传统商道到了老挝生活。据法国人记录,“1850年时,苗族人已在琅勃拉邦附近的山地区域建立诸多村寨,他们垦荒种地,种植鸦片。还同原在此地生活的老挝人、华人和掸族的马帮进行贸易。”由此说明,这些苗族生活的地方与马帮的商道有所重叠或就处在商道之上,由于马帮的路线通常是固定的,故苗族利用商道迁徙极为可能。据学者考证,“传统的沟通云南与东南亚的通道中,确实有一条是从云南进入老挝北部的丰沙里再由丰沙里南下到琅勃拉邦和万象,再由万象越过湄公河到泰国东北部地区”。可见,这种迁徙路径有一定的可取性。此外,也有一些苗族利用边地距离优势直接迁到与云南相邻的老挝北部生活。
(二)“国家化”的早期互动:在多势力间周旋
苗族进入老挝后,与不同政权主体的互动为其积累了丰富的群体经验,也为他们最终获得法定身份奠定了社会基础。
1.与封建国家的微弱联系
法昂(Fa Ngun)于1353年在川铜(今琅勃拉邦)建立了老挝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澜沧王国。苗族进入时,该政权已分裂为琅勃拉邦、万象和占巴塞(Champasak)三个部分,他们初到的丰沙里、华潘等省即属琅勃拉邦王国管辖。
但由于居住偏远,交通不便,苗族主要靠种山地、发展农业维持生计。这导致其与外界的联系相对较少,直接影响了他们必要的生活往来。彼时,苗族一般经济中只涉及极少部分的商业活动,如制售银饰、农具等,但由于这些物品通常很结实,这种活路也就不甚兴盛。所以,其基本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换也很少和当地社会发生关系,当需要盐、布等物资时,就等着来自中国的商人。一般情况下,每年苗族新年期间都有商人拿着货物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同苗族交换东西,这个过程中,由于一些人并不熟悉老挝货币的使用,有时他们就拿鸦片完成交易。这种状态使得苗族与老挝传统社会联系相对微弱,以至部分当地人都未关注到他们的活动。
2.对殖民管理的多重回应
随着苗族在上寮站稳脚跟,他们的存在逐渐引起地方政权的注意,尤其是印度支那沦为殖民地后,法国殖民者开始利用老挝的内部体系管理错综复杂的基层社会。
一是采取以老治老、以多治少的策略。1893年,法国借《曼谷条约》将老挝从暹罗属国变为“保护国”后,便将北部的琅勃拉邦视作王都,作为老挝的政治中心;在中部的万象设置副王,管理国家的国防、行政、财政;利用南部的占巴塞亲王,统筹社会福利。如此,用间接统治的形式,殖民者实现了“以老治老”的目的。彼时,长期的民族矛盾也已到了爆发边缘。为利用这种社会情绪控制不同力量,法国殖民者开始推行歧视政策,采取“以多治少”的办法,给予占人口多数的佬族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而对人数较少的民族则采取区别化对待,形成“民族等级制度”。这导致以苗族等为主要参与者的起义频繁发生。1896年,苗族因不堪忍受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繁重劳役,以川矿为中心发起暴动。1918年,苗族再次举起抗议大旗,在首领巴斋(Pa Chay)领导下发动武装斗争。
二是利用苛捐杂税增强自身管理权威。在建构殖民政治体系的同时,为满足经济需要,殖民政府开始对包括苗族等在内的山地民族课以重税,并迫使他们付出义务劳动。“19世纪初期,川圹地区的苗族在用现金支付税款的同时额外被追加每人一公斤鸦片,而到了19世纪中期,老龙人和老松人每人缴纳同一税款平均为9.60基普,老听人则为4.80基普。女人也未能幸免,她们被依据乳房的大小征收现金,一些怀孕的女性不得不避开市场、寺庙等人多的地方,以免碰上税收官。”
三是扶持不同势力,操纵政治图谋。随着苗族整体实力的不断增长,其内部的不同声音亦开始高涨,大家族间的明争暗斗逐渐从不易观察的地方影响他们的生活,分裂对立慢慢出现。罗比瑶(Lo Bliayao)家族和李峰(Lyfoung)家族的矛盾日趋公开化,法国人趁虚而入,利用他们之间的隔阂,扶植不同势力,分别委以官职,并给予一定的自治权,使其互不统属,分化管理。
殖民者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加强了对苗族的控制,极大地拉近了他们同殖民政府的距离,同时也部分强化了他们作为当地社区成员的资格,但事实上,因各类歧视政策的存在,苗族更多地只是被殖民当局作为制衡不同势力的棋子。
3.同王国政府的被动往来
1945年,因日本在印度支那发动军事政变,老挝短暂脱离法国控制,但很快,随着日军投降,法国重返老挝。于是,他们为延续在老挝的殖民影响,翌年便扶持原“保护国”琅勃拉邦王国的君主西萨旺·冯(Sisavang Vong)组建“老挝王国”政府,统辖整个老挝。
为拉拢苗族力量,官方开始将他们的上层精英安置进政府官僚体系。1946年,法国人任命杜比·李峰(Touby Lyfoung)担任川矿省苗族的昭孟(Chao muong)一职,同时将他的Tasseng头衔传递给其同父异母的哥哥。1958年,老挝第一次联合政府大选,杜比·李峰及其兄弟图里亚·李峰(Toulia Lyfoung)被选举为议会委员,费当·罗比瑶的家族势力也同期入选。1960年,杜比·李峰开始担任社会福利部部长,成为第一个出任内阁成员的老挝苗族。
与此同时,皇家政府也通过制定法律来保障包括苗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1947年,政府召开制宪会议,杜比·李峰被推举为国民代表,他由此提议修改宪法,最终当局承认老挝境内所有少数民族与佬族一样均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自此,苗族的法定身份得到初步承认。
(三)“国家化”的最终结果:法律身份的完全获得
法国重归的同时,美国为推行其国际战略,遏制共产主义发展,趁机插足老挝内政,并资助训练苗族军事力量,导致老挝苗族内部迅速分裂为对立的两派:一方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方追随以巴特寮为首的共产主义组织。后来,随着越战失败,美军退场,支持美国的部分苗族因担心遭到共产主义势力的清洗,遂越过湄公河进入联合国设在泰国的难民营避难。最终,他们被安置到美国、法国、澳大利亚、阿根廷、法属圭亚那等地。
留在老挝国内的苗族则跟随共和国的步伐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逐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当局尝试在短期内破除苗族地区的落后习俗,再以农业集体化为手段改变他们刀耕火种的耕作模式。同时,采取怀柔政策,呼吁隐藏在山林的苗族武装放下武器和解。其次,在居住环境、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良好的地方为苗族修建居民点并为其提供生活设施,吸引他们搬迁。第三,国家展开大规模“民族识别”活动,并依据实际情况将“苗族”认定为独立的法定少数民族,赋予其合法身份,保障其相应的社会地位。
此后,为促进“苗族”等少数民族向国家靠拢,政府持续推出系列措施。1982年,老挝人民革命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提倡各民族人民对国家与社会主义充满热爱,并增强国家意识,尽力消除民族与国家间的嫌隙。1991年,老挝人民革命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强调,民族问题是党、政府、人民都相当关注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团结是新时期老挝推进人民民主事业的关键因素。同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亦列出专门条款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后续召开的老挝人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延续了契合老挝国情的民族政策,会议报告认为,民族工作对于国家统一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持续促进各民族团结的同时,要防止民族间的矛盾出现,要使各民族群体认识到歧视其他民族或妄自菲薄都是不可取的。
紧接着,1995年,老挝公布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苗族”作为法定民族的资格被完全确认,并与前次一样同其他民族一起平等列出。彼时,他们的人口数量已位居全国第四。如此,老挝从党和国家的角度出发,不仅赋予了苗族法定成员资格,切实保护了苗族权益,而且不断推动他们与国家间的关系发展,有效促成了其向“老挝人”的转变。
三、社会身份生成的系列实践:苗族在老挝的“社会化”
苗族在老挝向国家靠近的过程,也是他们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前一阶段,苗族获得独立民族身份,同其他民族一起成为老挝社会的一份子;后一阶段,他们逐渐改变自身的生计方式,开始规模性参与当地社会的建设浪潮。
(一)“社会化”的政策准备
“国家化”不仅促成了老挝政府对苗族的有效管理,同时亦对其“社会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促使苗族向主流社会靠拢,老挝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积极拓展苗族的参政机会,有意识地在政府各类机构中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最明显的是,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55名委员中,即有5位苗族;而在国会的25位少数民族干部中,9人是苗族。与此同时,伴随老挝基础教育的全面展开,民族知识分子被迅速培养起来,各类研究机构和教育系统出现了一批苗族研究人员和教师。诸如此类的措施,确保了他们的法定权利,推进了苗族的社会发展,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强化了他们的社会观念,促进了苗族在老挝的社会化进程,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巩固,为后续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社会经验,奠定了他们参与社会建设的基础。
(二)“社会化”的生计融入
苗族在老挝的社会生境发生变化后,相应的生计模式也摆脱了历史束缚而变得更加多元,传统习惯与现代优势的结合使其生活姿态更为主动。
1.从殖民经济到市场经济
苗族到达老挝后延续了历史上的生产习惯,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自我生产成为满足群体社会生存的最主要手段。于是,在保障粮食种植安全的前提下,他们通过开垦山地、饲养家畜等途径维持着基本的生活需要。但这也导致其缺乏一定的经济作物。
法国侵入老挝不久,鸦片便被大面积引进至山地民族中间。1939年,杜比·李峰被法国人任命为农黑地区的行政长官,他大力倡导鸦片生产,使该地区成为当时老挝最重要的鸦片种植区之一,年产量增加到40吨。1944年,作为老挝苗族最重要的聚居地——川圹,已经成为当时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中最大的鸦片出产地之一,杜比·李峰亦成为法国的鸦片种植代言人。
这种生活持续了几十年,甚至于共和国成立后依然有部分苗寨进行鸦片生产,但随着国际社会的关注,一种更合适的经济作物——橡胶开始被大面积种植。从20世纪90年代起,老挝政府在中国等国际力量的帮助下,逐渐在北部山地推行替代种植计划,橡胶遂成为苗族重要的生计依赖。1994年,琅南塔省更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确立了橡胶在民生问题上的重要性。2000年前后,橡胶种植逐渐从北部地区向中部区域推进,各地苗族的生活发生了较大改变。
由于实行先占先得的政策,大多数苗族家庭都有数量不等的以公顷为单位的山地,这给他们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种植土地。以每公顷500棵树算,通常每户平均种植数都在1000棵以上,常呈现成片的橡胶林。根据笔者2020年的调查,每月每家至少有200万基普入账(约人民币1600元以上)。虽然受市场因素影响,胶价波动较大,但对他们而言,这一收入已相当不错。今天,橡胶种植已成为当地苗族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亦成为他们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苗族经济逐步从殖民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2.从乡土社会到旅游景观
近年来,老挝与中国、泰国、韩国、日本等国联系紧密,吸引了诸多游客到来。古朴的苗寨随即成为游人眼中的网红打卡地。万荣市郊的苗家村落即为典型。万荣属老挝万象省,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13号公路穿境而过,北去为著名的古城琅勃拉邦,东进可到首都万象,风光优美,素有“小桂林”之称,博得了大量旅客的青睐,成为老挝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当地居民借助旅游发展迅速获得了经济上的提升,居住在近郊的苗族亦分享了这一红利。
他们的寨子基本分布在距离市区约几公里的山脚下,规模大小不一。通过笔者对其中一处的统计,全村约78户,每户有5-10人,粗略估计,整个聚落人口在400-800人之间,相较其他地方属中等偏上规模。村子充分利用了距离优势,通过各种渠道将来万荣旅游的客人引至村中,不仅修建了部分具有田园风光的建筑,还将一些房屋粉刷成彩色,与传统房屋色调形成明显反差,给人以视觉冲击,借以营造旅游氛围。同时,利用附近的商店、饭店售卖土特产,一些人也通过种植蔬菜给城中的餐厅、酒店等供货参与了旅游业的发展,有些人还提供陪玩服务,收费每天100美金。
这些活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也让苗寨传统文化得到了释放,为其焕发新光彩创造了条件。当地苗族在自身需要与时代机缘的双重作用下积累了丰富的群体发展经验。
3.从本土谋生到出国就业
作为东南亚经济增长最具优势的国家之一,老挝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仅推动了自身社会的发展,也为区域内其他国家输送了诸多优质劳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外资纷纷涌入东南亚,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劳动力跨国流动。越来越多的老挝人选择出国谋生,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苗族人。
泰国是他们最常去的务工地之一。一位万象泰式按摩店的老板对笔者讲述了老挝劳工到泰国工作的情况:“老挝人到泰国工作的很多,因为两国在语言上没有太大的障碍,他们每个月去办理一次签证,花费几百泰铢不等的费用,或者去友谊大桥上出一次境,然后再入境就可以,这样花的钱少一些。他们(在泰国)的工资比在老挝要高,而且老挝的工作机会很少,在泰国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工作。”
调查期间,笔者曾遇到数位来自赛松本特区的苗族年轻人尝试通过中介公司到日本打工。其中,王苏赛家的案例较为典型。他家居住在阿奴翁县西北部的寨子里,2016年,初中毕业后的他经人介绍到万象的华人饭店工作,数月后因与其他员工发生矛盾,他在朋友邀约下赴泰国工作,之后在一处农场务工三年。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他随即失业回国。2021年初,他通过中介渠道进入赴日工作的面试当中,当年7月底,顺利出境工作。2022年,他利用在美国的亲戚关系,又介绍妹妹去美国打工。而在此之前,他的家族当中已有4人分赴不同国家工作,包括美国、韩国、泰国、日本。
由此,出国工作很可能成为打破苗族传统生计习惯的一个新方向。随着老挝工业化的发展,外资所能提供的工作形式将愈加多元,劳动力随产业转型到国外谋生将成为一种趋势。所以,“社会化”过程中苗族借助老挝国家的发展不仅促成了自我群体的融入,而且利用各种机遇使其国民身份更为巩固,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转换在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利的同时,也促成了他们社会文化的快速转型,未来随着时代步伐的推进或将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四、结语
“身份生成”的经历不仅表明了老挝苗族社会互动的复杂性,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亚历山大·温特的身份理论具有一定的扩展性。社会结构的变动促成了苗族成员资格的变动,也加快了其社会身份的构建,其中,族群身份的确立是老挝国家宏观观念结构作用于行为体本身的直接反应,并由此发生结构与行为体相互作用的双向驱动现象,最终行为体的身份特征逐步明显并进化为族群的集体身份。这解决了温特的理论关怀中身份生成与转化的重要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行为体依据“他者”视角不断塑造自我的过程。
但通过老挝苗族的实践互动可发现,行为体的身份构建事实上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向共时性过程转变的动态情景。前者主要涉及法定族群身份的获取,后者主要展现集体社会身份的形成,两者共同协调构建了苗族在老挝的国民身份。从这两个层面看,身份的形成既要关注历史条件,亦不能忽视现实环境,只有将二者并置才能完整拼接出个体及群体的身份构建过程。与此同时,“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共同作用还促使行为体不断向社会融入,并持续强化他们在国家秩序中的位置。正因如此,苗族在老挝的身份生成才一直表现得如此明显,并且发展成为一项集体行为,以致影响并重塑了老挝整体的社会结构秩序。
(摘自:鱼耀:《老挝苗族华人社会身份的持续生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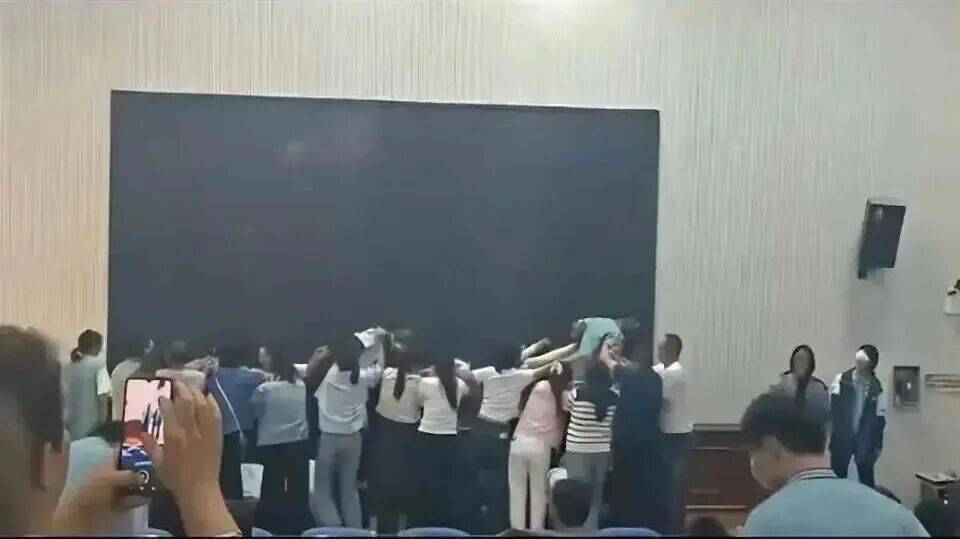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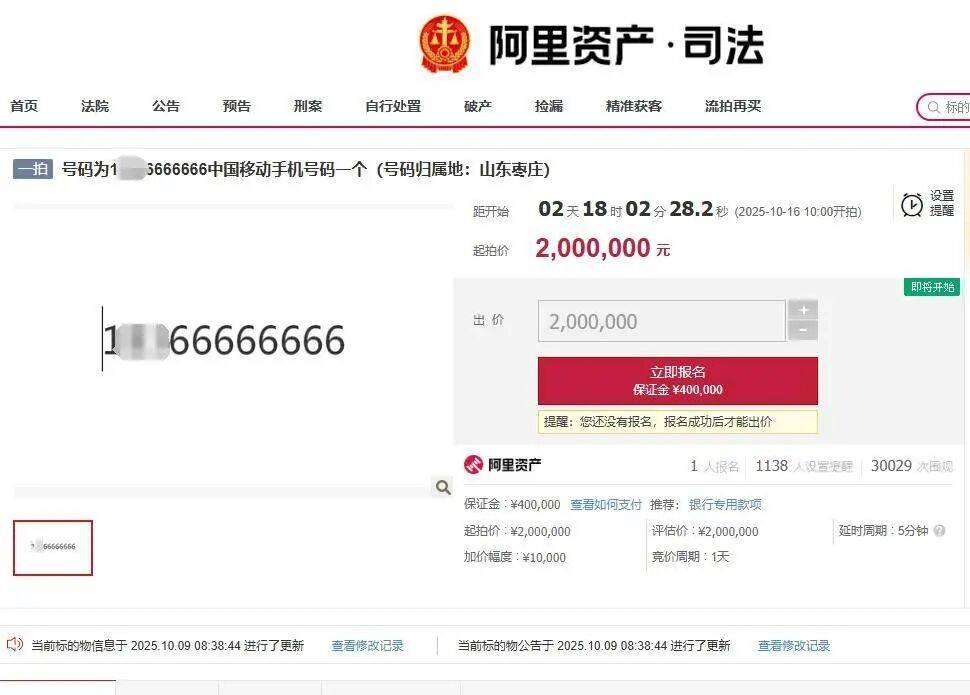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