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麦家:我害怕和年轻人说话,他们自有蓬勃的生命力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方涛 孙雯 实习生 陈嘉禾
1月26日傍晚,位于杭州西溪湿地的麦家理想谷,送走了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批读者。大家互道新年快乐,并相约2月4日之后,再来这里与麦家老师偶遇。
四天前的1月22日,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来到麦家理想谷,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在中国北方被惯称为“小年”,即使是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麦家并未缺席与读者的交流互动。
下午三点多通常是书店里读者最多的时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麦家习惯在这个时间走进读者中间,看看大家手头在读的书,聊一聊文学的话题。
“好多都是熟面孔了。”麦家与他们微微颔首,表示相互早已熟识。
虽然是工作日,读者也已几乎坐满,而每到周末更是人满为患。纸质阅读充沛的生命力在这方天地里清晰可见。而麦家却告诉记者,13年前,麦家理想谷刚办起来的时候,门可罗雀,哪怕来一个读者,大家都会激动很久。
是的。这个藏书一万多册,提供免费茶水、咖啡和创作场地,接纳五湖四海文学爱好者的公益性阅读空间,麦家已坚守了13年。正如他自己所言:“就像阳光融化山上的积雪一样,一点一滴的融化不易察觉,但热度够了,总是会引起雪崩的。”
在微博、小红书等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上,麦家理想谷的“热度”的确越来越高。这里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I人的精神家园”“灵魂得以栖居的场所”,全国各地的探店博主、阅读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来自北京的退休英语教师童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童女士对理想主义生活始终保持热忱,退休后,她有了更自由的时间,“我是最近才在视频号里关注麦家理想谷的。它本身的概念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带来一种纯粹的感动。昨天晚上我才落地杭州,在西溪附近住了下来,这几天什么景点也没有安排,就想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待几天。”
而遇见麦家完全是意外之喜。现场,麦家将自己的《人生海海》签名书送给这位远道而来的读者,并亲切地邀请童女士一起合影。离开后,童女士激动地在微信里给记者发来一句话:“不虚此行,很棒的经历!”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麦家理想谷发生。麦家坦言,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面前,自己则反其道行之,想给阅读者一个安静的角落,希望他们在阅读中获得一种安静的成长力量。

展开全文
麦家与读者在麦家理想谷合影
这也并非麦家第一次“反其道而行之”的执着。
近日,一段题为《人生海海,错了可以重来》的视频再次在网络走红,俘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心。视频来自麦家在2019年参加的“星空演讲”。
麦家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直面自己内心深处面对世俗名利的迷惘与痛苦,并真诚地对话年轻人,告诉他们,人生无处可逃,只有握手言和,走错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重新出发的勇气。
视频下的留言区里,年轻人纷纷留下自己成长的故事,相互激励着走出困境。有网友这样回复:“最让我感触的是麦家老师的真实,他能够看清楚自己的欲望并敢于承认自己曾迷失,事事优秀的精英固然令人惊叹,但有积难重返的勇气和执行力在我看来更难得……我们可以做那个开着破车出发的人,这应该是这个时代面对不平衡的社会现实下自我努力的叙事。”
麦家一向自称是个不善言辞之人。交谈中,他会停顿、沉思,但又总是真诚。真诚,恰恰也是他最新长篇力作《人间信》的主题之一。
作为一本从麦家心底喊出来的书,如果说《人生海海》讲的是天下事,《人间信》写的则是他的心里事。
这天下午,记者与麦家坐了下来,聊了聊他的理想谷、他与年轻人的对话,以及新作《人间信》。
以下是记者与麦家的对话:
【每个平凡人都有伟大的时刻】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在2019的“星空演讲”再次在网络走红,能否回忆一下您当时为何选择“错了可以重来”的主题?
麦家:2019年恰好是《人生海海》刚出版的那年,当时我整个心态还处在写作《人生海海》的情绪中。
那些年对我而言,即使不是人生的“滑铁卢”,至少也是跌跌撞撞的几年:父亲去世,写作遇到瓶颈,当时我停笔已经3年——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的黄金时间并不会太多,可我就是停了三年。
当我决定写《人生海海》这样一部和《解密》《暗算》《风声》完全不一样的小说时,确实冒着莫大的风险。因为换一个题材,换一个写法,甚至是换一种情感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一度是非常陌生和迷茫的。《人生海海》也写得非常艰难,断断续续写了五年。三年停笔,五年创作,整整八年才磨出这么一个作品来。
所以当时演讲里很多的内容,完全是我自己的经历。当然,这种经历是不那么愉快的,甚至是很苦涩、很痛,但又必须咽下去的,不能闭眼,不能回头,不能迂回。长达八年的这种人生体验,对我也是极其强烈的,我在演讲中,就把我怎么掉到坑里、怎么爬出来、又怎么另外找一个山头,重新出发的这种感受如实道来。
其实这个视频当初就打动了不少人。我看到,另一位演讲嘉宾当场就在抹眼泪。今天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个演讲?我觉得还是一种真实的意义。真实就是最动情的。
我其实没有演讲,而是在讲述自己的人生,讲述自己经受的苦难,讲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所有的力量其实都是从苦难当中历练出来的。如果我没有经历父亲的死,母亲长达半年的抑郁,我陪伴她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我也不可能讲述这样的故事。这种故事里涵盖着一种人之为人的艰难,而你能够从艰难中站起来,又表现了人之为人的伟大。
每个平凡的人都有伟大的时刻。这种情感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种情感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火。

麦家
潮新闻·钱江晚报:几年过去,它依然激励着无数年轻人,对此,您怎么看?
麦家:说句实在话,我害怕对年轻人说话。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个年代完全不一样。当年的我们特别需要长辈的引导和依靠。但现在,巨大的互联网和信息场给他们的能量远远大于某个具体的长辈。
现在的年轻人不需要教育,他们只需要陪伴;甚至他们也不需要陪伴,他们有自我的蓬勃的生命力。
但我也想谈一点自己看到的:现在年轻人的幸福指数远远没有我们年轻时高,尽管我们当时物质非常匮乏,也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举个例子,我们村庄有6000人,是当时富阳最大的村庄。但村里,机械化的物件唯有两辆自行车和两部收音机,而它们又都在两家人手中——他们在县城里有工作。我和我的同龄人就是在这样贫穷落后,甚至是愚昧的环境里长大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好时代。80年代改革开放,祖国欣欣向荣,确实有各种各样等着我们去发现、创造、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甚至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今天,似乎留给年轻人创造的机会和价值的空间已经不大了。现在的年轻人不但要自己拼搏,咬紧牙关,同时还要天助。
面对这样的时代,面对信息源如此之多、自我成长特别发达的年轻人,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当他们的老师吗?除非我能当他们的老天,给他们机会,他们才可能听我的。他们也一点都不缺乏成长的力量,他们需要的是空间和机会。
潮新闻·钱江晚报:《种地吧》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档节目,您也经常去探班。第三季您有没有去?有没有发现这十个年轻人的一些变化或成长?
麦家:第三季我还没有去。我跟十个勤天确实是有缘,这种缘分来得非常突然。我可以说是最早去探望十个勤天的飞行嘉宾。某个冬天,张绍刚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陪他去看一些年轻人?具体是什么年轻人他没告诉我,我就这么成为他们的第一个飞行嘉宾。
我至今还有印象,我告诉他们,作家在心灵上耕耘,你们在大地上耕耘。中国历来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耕和读就是一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十个孩子聊天,给他们鼓励。后来,策划工作者从我们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些灵感。某种意义上对他们的成长也是一个牵引。
结下缘分以后,我有机会就会去看看他们,还专门给他们做了个图书角,亲自定制了书橱,买了大概两三百本书。我说,你们一边劳作,千万不要忘了读书。我也带他们来过麦家理想谷,让他们见识普通读者是如何在阅读中获得力量的。
【用时间回馈文学的给予】
潮新闻·钱江晚报:最近麦家理想谷有了更多读者,有自媒体人,也有普通的阅读者,我们也看到了您与大家的互动,在您看来,作家、书店、读者的关系是什么?您在忙碌的创作间隙,如何参与这种互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让您感动的瞬间?
麦家:理想谷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标签,但当初建它的时候,其实只是出于一种内心的需要。
2010年我回到杭州。当时,我已经获得茅奖,电影《风声》也好评如潮,我的作品无论是出版、影视化改编全都炙手可热。当巨大的名和利袭来的时候,我内心一直很惶恐。一种朴素的声音在召唤我:文学给了你那么多,你是不是应该拿出来还给文学?
于是我建立了麦家理想谷,完全没想到它有一天会火,只是让它一直陪伴着我,我自己也陪伴着它。这里有一个特点是一切都免费,唯独不提供免费的WiFi,就是为了鼓励大家读书。
一传十十传百,麦家理想谷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来的人越来越多,成为一个杭州的“文化打卡点”。我对它变成爆款并不意外。我是个慢性子,耐得住寂寞,坚持了整整十三年,也非常愿意为它付出。只要我在这儿,每天下午三到四点,我会过去跟读者们见个面。这种滚雪球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付出,对这种付出有好感、有认可的人就会慢慢聚集起来。

麦家与读者交流
潮新闻·钱江晚报: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让您感动的瞬间?有没有一两个老面孔让您印象深刻?
麦家:太多了,不是一两个,至少四五十个。这里现在有很多固定的读者,甚至写作者。从这里走出了好几个作家,有一位写作者至少在这里写了三年。她写的长篇我也看了,第一稿是66万字,我提了修改意见后改成55万字,到现在都还在改。老读者也很多,昨天我去拍照的时候,至少看到三张熟悉的面孔。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都是老朋友了。
【麦家:我们这代人有个关键词叫坚强】
潮新闻·钱江晚报:小说探讨了一个极其深刻而严肃的问题——当血缘、伦理和价值观冲突时,人该如何抉择。结尾章《众声》,尽管仍以主角之名叙述,读来却更像是一则后记,仿佛揭露了创作的心路历程,能否谈谈您写这一章的考量?
麦家:在这部小说的结构上,我确实做了一些探索。《人间信》中间的六个章节都有两个小标题,但第一章叫《绳子》,其实就是引子的意思;最后一章叫《众声》,其实也就是尾声的意思。
从结构上来说,引子、尾声都是主体的装饰物,好像音乐中的过门,把它拿掉也无妨。不过,最后这一章我的表达特别直接,作家在这里完全可以跳出小说写自己,尽管自己仍然是作品里面的自己,但作为作家的“我”和作为人物的“我”在这里结合的自由度特别大,提供了表达的方便和自由。
潮新闻·钱江晚报:“背叛”和“忏悔”是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父亲对家族仇恨、国家仇恨的背叛,最终导致了奶奶的离去;“我”对父亲的背叛,导致了家族分崩离析。父与子的关系,通常是敏感而微妙的,为何会选择这个直面心灵的题材深入挖掘?
麦家:《人间信》写的是我内心非常深的地方。聊这部作品就像让一个人聊他的失恋或者失败的婚姻,都是生命之痛,一般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但我仍愿意为文学献身,世俗的成功给了我勇气,让我去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困难,甚至是羞耻。
很多人把《人间信》看作我的准自传,我是极力反对的。我虽然没有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但也没有如此糟糕;我的父亲确实没有给我带来幸福感,但也绝不是小说里的“潦坯”。
这部小说通俗一点、概括一点讲,写的就是“我和我的潦坯父亲”这样一个故事:主角在父亲的阴影下成长起来,叛逆成为他成长最大的力量。但这种成长并非顺风顺水,而是有很多抗拒、冲突,甚至耻辱、出卖父亲。这是一种痛苦的成长,而我们这代人恰恰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我们的成长道路真可以说是饱经风霜、历经坎坷,但是我们确实从来没有认输过,一直在倔强地挺进、困难地成长。这种困难当中,既有体力上的辛苦,更有内心的煎熬,在道德面前经受的考验和打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印记。
我想代表我们这代人写一部作品,他们的内心或许不像今天的年轻人那样敞亮,但在困难面前特别有爆发力,也特别坚强——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坚强。如果给我们这一代人总结关键词,其中一个肯定会是“坚强”。

麦家
潮新闻·钱江晚报:《人间信》是一部跨越四代人的家族小说。可以说,小说既是一部心灵史,也是一部家庭史,为我们展现了乡村宗族家庭的全景。其中,数铁钉的“家法”数次出现,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从奶奶到母亲,执行“家法”更像是某种家庭权利的轮替,为何会设计这个意象?
麦家:一部长篇小说的细节确实不能泛泛而谈,作者一定是处心积虑,有设计有讲究的。
就“家法”这个细节而言,小说里先是奶奶要行使爷爷的宗族权利,因为爷爷去世得早,奶奶是既当爹又当妈的。它映射的是男权社会下,家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惩罚,而是农村农业社会的道德阵地。小说最后母亲到了部队去见儿子,也带上了家法。
“我”出卖了父亲,认为父亲如此不堪、如此混蛋,所以告发了他。“我”以为是给家庭除了毒瘤、替母亲替奶奶争了气,殊不知在传统的伦理社会当中,这是大逆不道。母亲就是接受了这种传统思想,从此不认这个儿子了,即使最后决定要与儿子和解,也必须给“我”一个刑罚,这代表着让“我”承认出卖父亲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即使父亲出狱后更加不堪。
“家法”是对传统的一种刻画。现代社会正是从传统社会发展过来的,我们其实一直都处在传统的枷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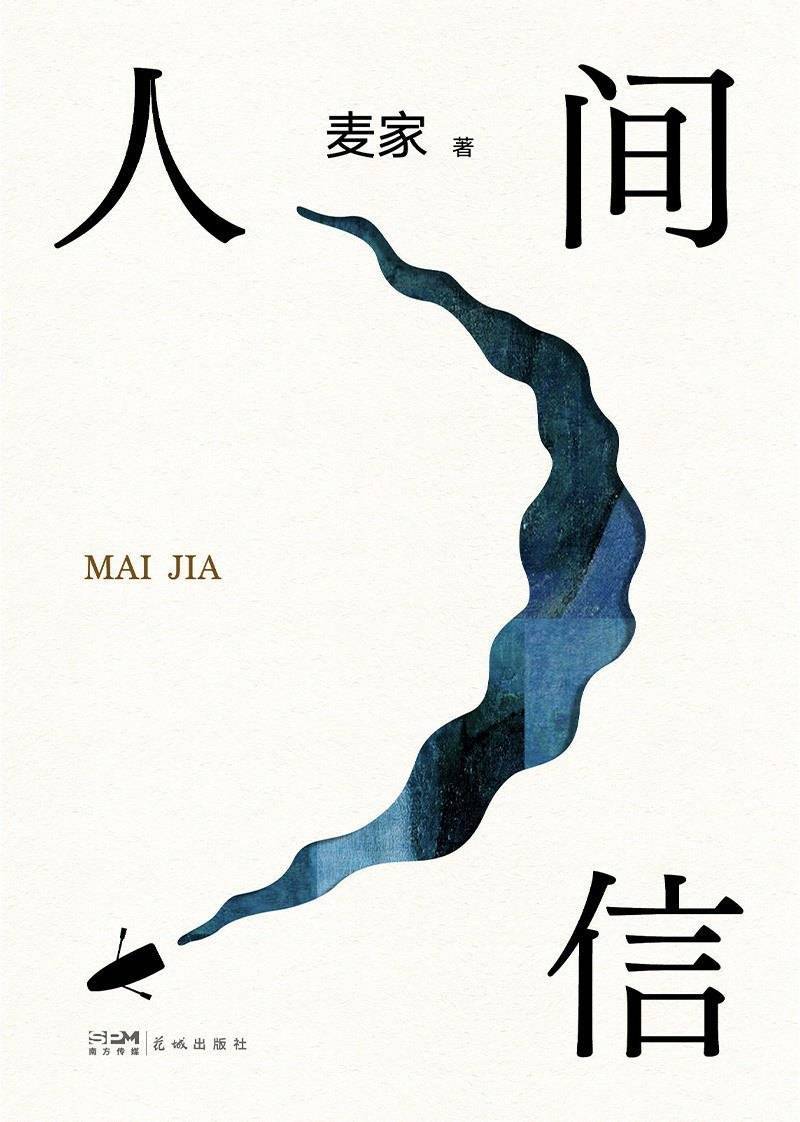
《人间信》麦家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潮新闻·钱江晚报:什么时候决定采用《人间信》——这个有点像非虚构的名词作为书名?
麦家:这部小说我写了五年,期间我想过太多标题了。
最初冒出来的名字是《呜啊呜啦》,这是一个哭的拟声词。大概写到第四年,开始写倒数的第二章的时候,我决定要用这个名字。这部小说是一部很凄楚、悲情的小说。虽然“我”成长了起来,但成长的过程却充满了罪恶与冲突,是撕裂性的、凄惨的。可以说,这本书里面人人都在哭泣。
我当时为这样一种想法所痴迷: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拟声词。但哭的拟声词没有固定下来,比如“呜呜呜”,很潦草。我当时有这么一个信念,想通过这部小说,把哭的拟声词提炼出来,固定下来。这也是受到了《人生海海》的鼓励,这句闽南俗语,在小说出版之前,流传度很低。如今,在年轻人中已经成为一个“热词”了,大家都很喜欢引用。不过,这个想法最终受到很多朋友的反对:大家觉得你辛辛苦苦写了五年的作品,在书名上冒这么大的险是不值得的;同时,作品本身已经悲苦,还是要在书名里人一些勇气和力量,最后就放弃了。
我在尾声中也提到,我最近一直在看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的诗,她有一首诗写道,“伤口释出自己的光/如果屋里的灯全都熄灭/你能用伤口放出的光/把它穿戴起来”。这首诗给了我灵感,我想了个书名叫《伤口之殇》,也用了很长时间。这些年,我也看了很多乔治·斯坦纳的书。他有一本自传叫《勘误表》,我当时也想用《勘误书》作为书名,对自己人生的检错,很切题。但显然过于拗口和学究了,也被推翻了。
想过的书名其实还有很多,但用得比较久的是这几个。后来就想到《人间来信》,最终简化成了《人间信》。
潮新闻·钱江晚报:从《人生海海》到《人间信》,您的“故乡三部曲”已有两部与读者见面。下一部的创作已经在构思中了吗?听说您最近还准备写一部武侠小说,能否给广大读者透露接下来的创作计划。
麦家:创作计划当然是先把“故乡三部曲”的第三部写出来。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已经写完了,但初稿对我而言仅仅是个开始。我的作品都会反复修改,因为我坚信好作品是修改出来的。
世上大概有两类作家:一类是喷射型,靠才华写得泥沙俱下,一气呵成;另一类就是慢慢修炼的类型。我曾经谈过一本书叫《巴托比症候群》,是西班牙作家马塔斯的作品,谈到很多作家、艺术家、导演、音乐家最开始都才华横溢、出手不凡,出来就是一个高山仰止的作品,但后来反而不写了,消失了。我则是那种慢热型的作家,成名晚,但也有更持久的情感力量。
今天我依然觉得我的写作没有达到顶峰,仍然在攀登。从《解密》《暗算》《风声》“谍战三部曲”跳到“故乡三部曲”,现在还没有写完,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说到武侠小说,这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巨大门类。但今天,金庸、梁羽生构建的“成人童话”式的武侠小说,受众已经越来越少,年轻人并不热衷。我想,能不能对传统武侠小说进行改造、重新发明?其实已经断断续续做了近十年的准备,我确实心有此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转载请注明出处”









评论